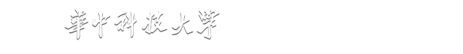通讯员:尹圣威 编辑:舒年春 责任编辑:叶金州 杨海斌
2021年11月29日晚19点,华中大-海德堡大讲堂哲学专场暨慧源哲学海外名家大讲堂第2期在js333金沙线路检测登录入口博闻厅(东五楼435)举行。邀请耶鲁大学哲学系ThomasPogge教授主讲“如何思考全球正义(Howto Think about Global Justice)”,院长助理叶金州主持,雷瑞鹏教授担任点评嘉宾。Pogge教授为著名哲学家罗尔斯的知名弟子,是当代国际学界全球正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讲座线上线下同时进行,40余位师生参加。
Pogge教授介绍了正义这一概念的历史。在西方哲学史上,正义一词最初被定义为一种个体的美德:正义表现为一个人按照他人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人,而正义的本质则是个体拥有的良序的内部结构(well-orderedness)。柏拉图对正义的含义作了拓展,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与正义的个体类似,只要满足拥有良序的内部结构,一个城邦或国家同样可以是正义的。后来,罗尔斯把社会正义定义为财产的分配制度,或社会的“基本结构”(basicstructure)。所谓“基本结构”,指的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或法律系统的组织形式。
Pogge教授说,在罗尔斯看来,因为正义对分配有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所以对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进行道德分析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设计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机会、收入、责任、权利以及义务的分配。对基本结构的设计包含着实质(substance)和程序(procedure)两方面的道德要求:实质上的道德要求,指的是它们应当如何被设计;程序上的道德要求,指的是应当由谁来设计它们。因此,罗尔斯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社会基本结构应该如何设计?又应该由谁来决定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
Pogge教授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不完整的。我们应当把社会正义的范围,拓宽到其他具有结构特征的领域:例如社会实践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的物质环境。这些领域不仅能够明显地影响分配,而且同样可以被人类设计、决定,所以它们同样具有实质上和程序上的道德要求。Pogge教授指出,超国界(supranational)领域也具有这样的结构性特征,我们应该把有关正义的道德要求延伸到超国界领域:例如国际制度安排、国际惯例、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全球正义就是对“世界如何社会性结构设定” (sociallystructured)的道德评价。对“世界如何社会性结构设定”的回答包含两层含义:
这个结构是怎样的?
谁来进行世界的社会性结构设定?即谁拥有力量参与世界的社会性结构设定进程?
随后,Pogge教授讨论了全球正义的重要性,举例展现世界贫困差距问题,以及为什么存在,并提出了理想性的解决思路。
同时Pogge教授指出实现全球正义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人们拥有不同的正义观念(conception),世界各处的人们很难完全认同一个特定的正义理论。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上存在大量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正义提出的迫切的道德要求和政治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在Pogge教授看来,任何有关全球正义的理论都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核心要求,即一个正义的超国界结构(supranationalstructure)必须尽可能的满足如下要求:
让当今时代的所有人,以及未来时代的人类过上值得过的生活。这个要求也有如下表述方式,如人类需求(马克思)、基本自由(康德/罗尔斯)或人类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任何全球正义理论而言,这个核心要求都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优先性(priority),即这一核心要求优先于一个全球正义理论中的任何其他原则。
二是重叠性(overlapping),即任何不同的全球正义理论,都必须以承认这一核心要求为基础。
Pogge教授谈到,虽然这个核心要求本身不包含平等,但我们可以把这一核心要求拓展到另外两个有关平等的维度:实质上的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和程序上的公平(procedural fairness)。
Pogge教授阐述了竞争/对抗系统的优缺点。列举了福布斯富豪榜的数据,想来说明西方经济精英们权力的膨胀有多迅速,讲座中,还引用了经济学者RaquelAlexander等人的研究,来确证全球正义问题的重要性。
Pogge教授的讲座结束,雷瑞鹏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总结并给出点评。随后,进入了提问与讨论环节。互动环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大家还就当今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
最后,叶金州老师为本次讲座作了总结,并感谢ThomasPogge教授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热情的参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活动。
第二期慧源哲学海外名家大讲堂顺利结束。
注:交流提问摘录(部分)
提问1:问:作为研究全球正义和罗尔斯的学者,您怎么评价马克思的正义理论?
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将给出回答这一问题的几个思路:马克思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他对社会如何设定其结构,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如何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很深刻的思考,例如他的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关注的更多是社会结构产生的后果,而罗尔斯认为,我们有更大地自由去决定如何设计社会的结构。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是确定且连续的。罗尔斯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结构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慎重的思考如何设计社会结构,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繁荣。罗尔斯将马克思的理论带入了美国,在罗尔斯之前,美国人是很少关注社会结构的。美国人往往认为一个人的富裕或贫困,都是他自己行为导致的结果,如果每个人努力工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富裕。不关注社会结构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罗尔斯虽然没有提到马克思,但他把马克思的理论内核引入美国,使得美国人开始关注社会结构的设计。
问:所以我能否理解为,罗尔斯强调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设计社会结构方面的重要性,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决定论(determinism)态度,认为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遵循确定的规则?
答:我不喜欢用“决定论”一词,因为社会结构的发展只是一个有条件限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并不一定要发生在法国,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德国、意大利等国,能确定的只是最基本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发展逻辑。所以马克思也相信人们拥有自由,只不过需要在最终消灭阶级社会之后,这种自由才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讨论的不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提问2:
问:如果您认为最富裕的人口应当救助贫困人口,那么您的理论是关于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吗?您的理论是否有些过于理想化,从而忽视了现实性呢?我喜欢您的作品《理解罗尔斯》,但我认为与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理论相比,您的理论是更难以实现的。
答:首先,罗尔斯并非一个平等主义者。如果读过他的作品《万民法》,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提到平等主义。他认为资助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生存的最低需求,是一种责任。我曾批评过罗尔斯的这个观点。因此我想说的不是,我比罗尔斯更像是一个平等主义者,而是就全球正义这个层次来说,我是一个平等主义者,而罗尔斯不是。
另一方面,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面对一个极度不正义的世界,一个被极少数精英按照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统治的世界,我们应该从何着手进行让世界变得正义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必须一步步地斗争,一步步地改变现在的结构。我的一个想法是影响力基金(impact-fund):我们注意到,知识产权是现有的不平等得以积累和扩大的一个重要方式。如果我拥有一项知识产权,那么任何使用这个产权物的人都要向我支付费用。这样的做法与封建主义很像,如果我有一块土地,那么任何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都要向我支付一半的收成。这样的制度把占大多数的不具备支付能力的人排除在外,不平等和贫困由此产生。我想做的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一点小小的改革,即持有知识产权者根据产品带来的影响,获得相应的资金收益。例如,药物专利应该按照使用此药物后康复的人数来获得相应收益。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它产生的影响足以使社会结构向着更平等的方向变革。我不认同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来改变社会结构,我认为需要做的是对当前规则施加政治和道德的压力,一步步地斗争,为分配的平等争取每一寸土地。
提问3:
问:如果普遍主义是您理论的基础,那么您如何回应普遍主义受到的批判?
答:我认为普遍主义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有多个不同的理论,而一个理论可以被所有人接受,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普遍的。另一方面,普遍主义指的可能是一个对所有人的权利和责任提出相同的要求的理论。前者强调的是理论的范围,即这个理论应当覆盖所有人;后者强调的是,这个理论覆盖的人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被对待。我认为问题中提到的普遍主义问题指的应该是第一种情况。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世界是如何设定其结构的,这个问题涉及每一个人,例如气候变化,疫情流行,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等。这些问题亟待回答,而且只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答案,我们才能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并非在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个普遍主义的回答,而是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普遍的,回答这些问题要求给出一个所有人都接受解决方式。对于某一个全球正义的理论,我们当然可以表达赞同或反对的态度,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观念。然而对于全球正义理论所要求的设计世界结构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能仅仅只表达赞同或反对的态度,因为这里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结构化。

 学院微信公众号
学院微信公众号